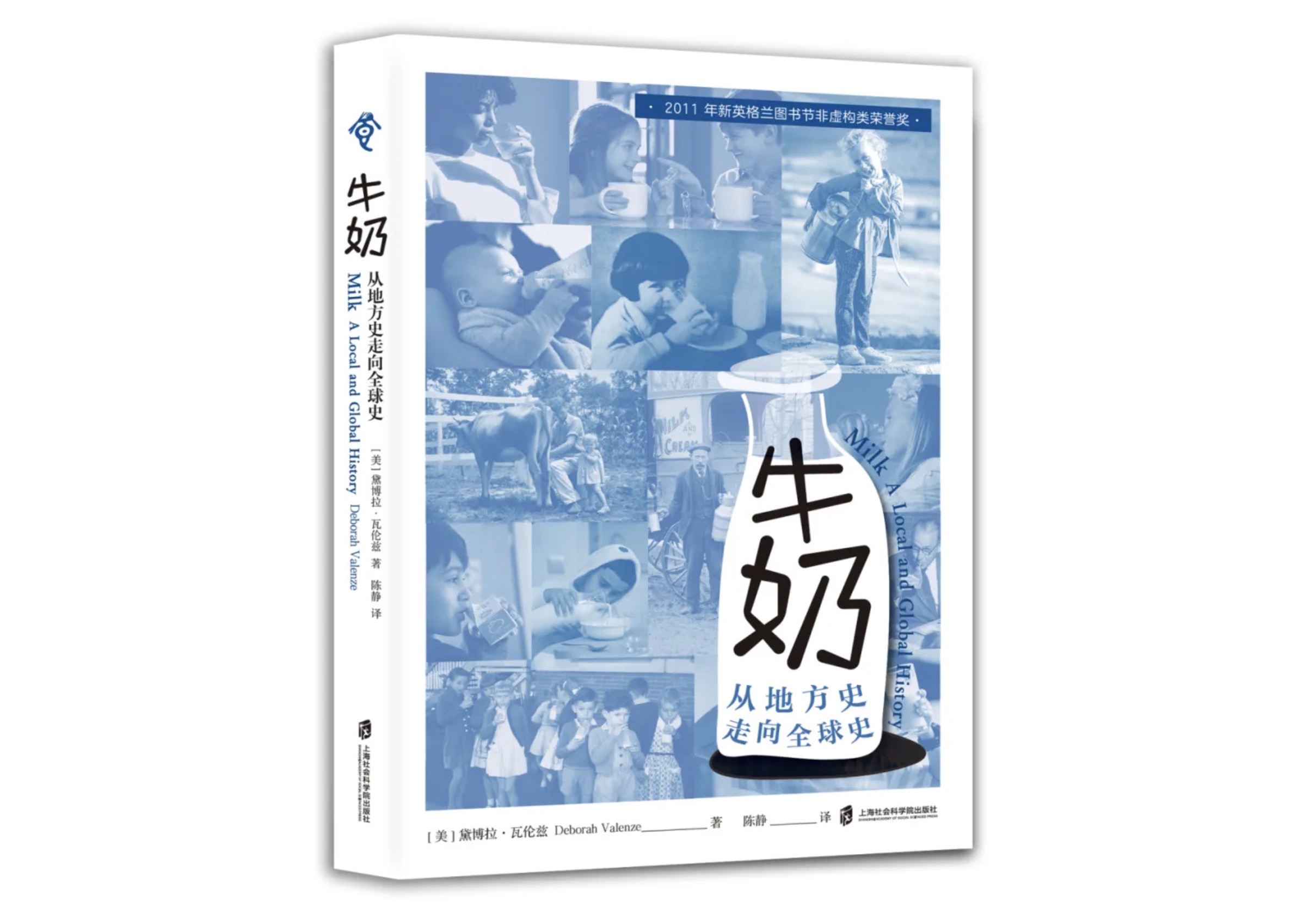
从宗教仪式到家庭餐桌,从农场到全球市场,牛奶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牛奶:从地方史走向全球史》一书,探索了牛奶从古代祭祀到现代工业的奇妙旅程,深入挖掘了这种白色液体如何渗透文化、塑造社会,并成为科学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象征,甚至被现代营养学奉为“完美的食物”。
让我们在引人入胜又诙谐幽默的叙述中,重新认识牛奶这一日常饮品。
-书摘-
一杯洁净的牛奶为何令人震惊?
在1900年巴黎博览会上出现的诸多著名奇迹之作中,有两件展品令人意外的朴素不起眼: 从伊利诺伊、纽约和新泽西进口的牛奶和奶油,“未经加工、处于自然状态且未采取任何保鲜措施”,“就如同刚从奶牛身上挤下来的鲜奶一样纯净甘甜”。在两个多星期的长途旅行中,这些产品甚至经受住了巴黎和乳制品博览会附近万塞讷(Vincennes)耗时颇长的海关检验。美国人每天往展会上提供新鲜的样本(他们也是博览会上唯一这样操作的参展者),以强调他们精湛表演的可靠性。他们的成功更多的是源于简单的清洁卫生,而并非现代技术。这个故事体现的价值已经不言而喻: 在1900年,无论与奶牛的距离相隔多远,纯净的牛奶都会引起人们的惊讶。
实际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大众的普遍意识中多将牛奶与疾病联系到一起。这种看上去洁白无瑕的液体吸收和滋生细菌的能力堪比任何实验室的培养皿。持续不断的有媒体报道将它与结核病和其他流行病联系到一起: 牛奶频繁成为白喉、猩红热、脓毒性咽喉炎和伤寒等病菌的宿主(可以通过牛奶传播的疾病远远不止这几种,还包括其他许多病毒性和细菌性的疾病)。
在这些疾病中,只有结核病始发于奶牛,其他病菌都是通过受污染的表面和人的双手与牛奶结合到一起的。牛奶腐坏变质一直是人们担心的问题,而工业化学时代,消费者又面临了一种全新时代的危机。农民和经销商依赖的添加剂在我们听来更像是汽车上用的那些液体,如冷却液、保鲜液、冷冻液,以此来延长未冷藏储存的牛奶的保质期。这些添加剂的主要成分是甲醛和硼酸,可以杀死许多被我们笼统地理解为“细菌”的杂质: 包括在从奶牛到消费者之间的运输过程中混入产品中的粪便、死苍蝇和其他一些污垢。这就难怪,在1900年,博览会上出现的纯净牛奶可以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
看似洁白实则危险的“细菌培养皿”
19世纪的人们对酸腐牛奶的味道并不陌生;更何况实际上在某些地区,酸腐的牛奶制品甚至是许多人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牛奶变酸的情况下,其中所含的过量乳酸实际上并不一定会使消费者生病,但这种腐败现象通常表明,潜伏在产品中的外来细菌可以在短短的一两天之内成倍繁殖。
然而,味道和气味并不是检验致病细菌的可靠标准;当公众对数字和数据无动于衷时,改革者们就开始沉迷于用有关受感染的奶牛乳房渗出脓液的骇人听闻的描述来引起反响。隐忍或被蛊惑的消费者便可能在事后开始对牛奶的供应产生质疑: 牛奶传播的疾病如果在某一个社区频繁发生,则可以准确定位该社区的地理位置,最终会发现,那里的某个牛奶供应商甚至是送奶工就是该地区白喉或肺结核大流行的源头。毋庸置疑,化学和医学研究人员在解决牛奶相关问题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但令人困扰的问题是,指导方针和法律究竟应该如何规范这一角色。
巴氏杀菌的科学介入为何如此缓慢?
现代消费者可能会对路易斯·巴斯德这位传奇人物在牛奶事业中所起的微不足道的作用感到惊讶。19世纪60年代,他当然没有在实验室里彻底改变牛奶的营销方式。的确,他发现了一种叫作“微生物”的极小生命体,正是这种物质使消耗性液体变质。通常,加热可以杀灭微生物或降低它们的有害影响。但考虑到当时还处在一个没有接受现代流行病学教育的世界(更不用提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了),这些研究的影响力有限,也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所熟知的巴氏杀菌法,经历了60年才成为普遍被采用的生产工艺。微生物在被发现后,至少经历了20年,才成为牛奶改革者的关注目标。由于巴斯德起初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葡萄酒和啤酒,所以要把研究成果运用到牛奶上,还需要大量额外的工作。值得称赞的是,一位德国农业化学家弗朗茨·里特尔·冯·索格利特(Franz Ritter von Soxhlet)在1886年就设计出了工作能力令人满意的设备。他之所以在编年史上显得默默无闻,也许是因为如果以他的姓氏来命名一个专业术语,那么听上去似乎并不那么专业。
巴氏杀菌法其实要求相当简单。这种工艺需要保留牛奶标志性的质地和口感,所以应避免过度加热。而且,由于温热的牛奶非常适合微生物的进一步繁殖,所以在用加热杀灭大部分细菌的过程结束以后,紧接着就必须对牛奶进行迅速冷却。整个灭菌过程大约是使用140华氏度的高温持续加热20—30分钟,某些制造商偏爱使用更高一些的温度,但后来证明过高的温度会破坏牛奶中的某些特性。(现代的操作使用温度更高,通常能达到162—165华氏度,但加热时间仅持续15—20秒)。随后,奶液需要马上进行冷却并倒进无菌的容器中,加盖干净、密封性好的瓶盖,并始终保持低温。
另一种方法就是通常所说的“灭菌”,即将牛奶持续煮沸一段时间。经过消毒的牛奶配上带有白色涂层的牛奶瓶包装,以确保产品给人一种无菌的印象,还带有一丝实验室的光环。这一工艺在英国、德国、法国相当流行,在美国也算是相当流行。然而,在一般公众看来,这些特别的措施似乎太过昂贵和繁琐。利用商业设计的设备,并仔细注意操作程序的话,巴氏灭菌也可以在家中进行,但仍然是成本不菲。
百年前人们为何不信“灭菌牛奶”?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初,巴氏杀菌法的方方面面都存在费用和技术障碍,更不用说大众对它普遍存在的怀疑态度了。巴氏杀菌法发展缓慢,并不是因为缺乏化学家的专业建议、设备仪器甚至资源。100多年前的人们也像今天的大众一样,出于种种理由,支持和反对这一工艺的热情都极其高涨。
一些热情拥护干净牛奶的人反对巴氏杀菌法,因为这种方法拥有原谅肮脏、包容邋遢懒散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些人质疑它对牛奶产生的影响,认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牛奶中的“酵素”(天然酶)会被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考虑到当时维生素还没有被发现,我们不能补充说其实这一过程也会破坏一些维生素成分)。
还有一些人不喜欢经过巴氏杀菌和灭菌的牛奶的味道,因为它们缺乏真正的牛奶爱好者从天然产品中很容易就能识别出的香味和醇厚感。许多奶农和供应商都坚持否认牛奶需要经过特殊的处理,声称他们的牛奶即便是以生牛乳状态直接供应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化学家们自己也开始对巴氏杀菌的正确程序产生了争议。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几个国家中爆发的地方斗争暴露出潜在的财政困难: 实现无害牛奶的供应所需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如何使这一生产过程规范化和接受严格的监管?由于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缺乏共识,直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普通民众在市场上都没有获得安全牛奶的保障。
这些都是现代牛奶摆脱困境的关键时期。疾病的威胁是这种商品及其生产者被迫进入了关于公共卫生和国家责任的新的重要辩论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牛奶和被广泛使用的婴儿配方奶粉之间的紧密联系,纯牛奶的问题被提上了所有食品安全问题的首要位置。科学和儿科医生在确定这种珍贵白色液体的未来发展方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卫生焦虑:全民建立微生物防御体系
这些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 经过改良的牛奶生产方式将牛奶扩大成了一种普遍可消费的商品。由于纯度、冷藏、包装和运输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市场化牛奶的生产得以完成。对牛奶纯净度的追求把我们带入了20世纪,那时,牛奶变成了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商品。
19世纪最后40年左右的时间,被一种特殊的偏执氛围笼罩着,它可以用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汇来概括: 卫生。稍微夸张一点说,如果当时世界上不存在巴斯德这个人,那么卫生学家们都有可能会想尽办法把他发明出来。历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巴斯德发现了微生物可能带来的威胁,这使得人们甚至在还不了解一滴牛奶的内部构成机制之前,就开始对物理环境产生普遍性的不安。
老一辈的欧洲人使用卫生改革来应对一波又一波传染病的流行浪潮: 这主要体现在对城市中“藏污纳垢”的贫困街区进行打击上。巴斯德之所以驳斥亚里士多德关于导致疾病的病原体是“自然产生”的这一理论(这一概念实际上引入了“疾病是由病菌引起”的理论),是基于长期以来对环境的焦虑。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发现的细菌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这引发了一场针对所有环境(包括普通家庭内部环境)的攻击。一个由医生、科学家和政府组成的大联盟全体动员起来对抗微生物入侵,仿佛在与成千上万隐藏的敌人作战。拉图尔告诉我们,“‘传染病’‘瘴气’,甚至‘尘土’等模糊的词汇就足以让欧洲陷入困境。”“食物、城市化、性、教育、军队,这些词汇反而激不起他们的兴趣,因为人们对它们感到陌生。”整个世界都不得不为对抗微生物的战争“腾出空间”。
头图为《牛奶:从地方史走向全球史》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