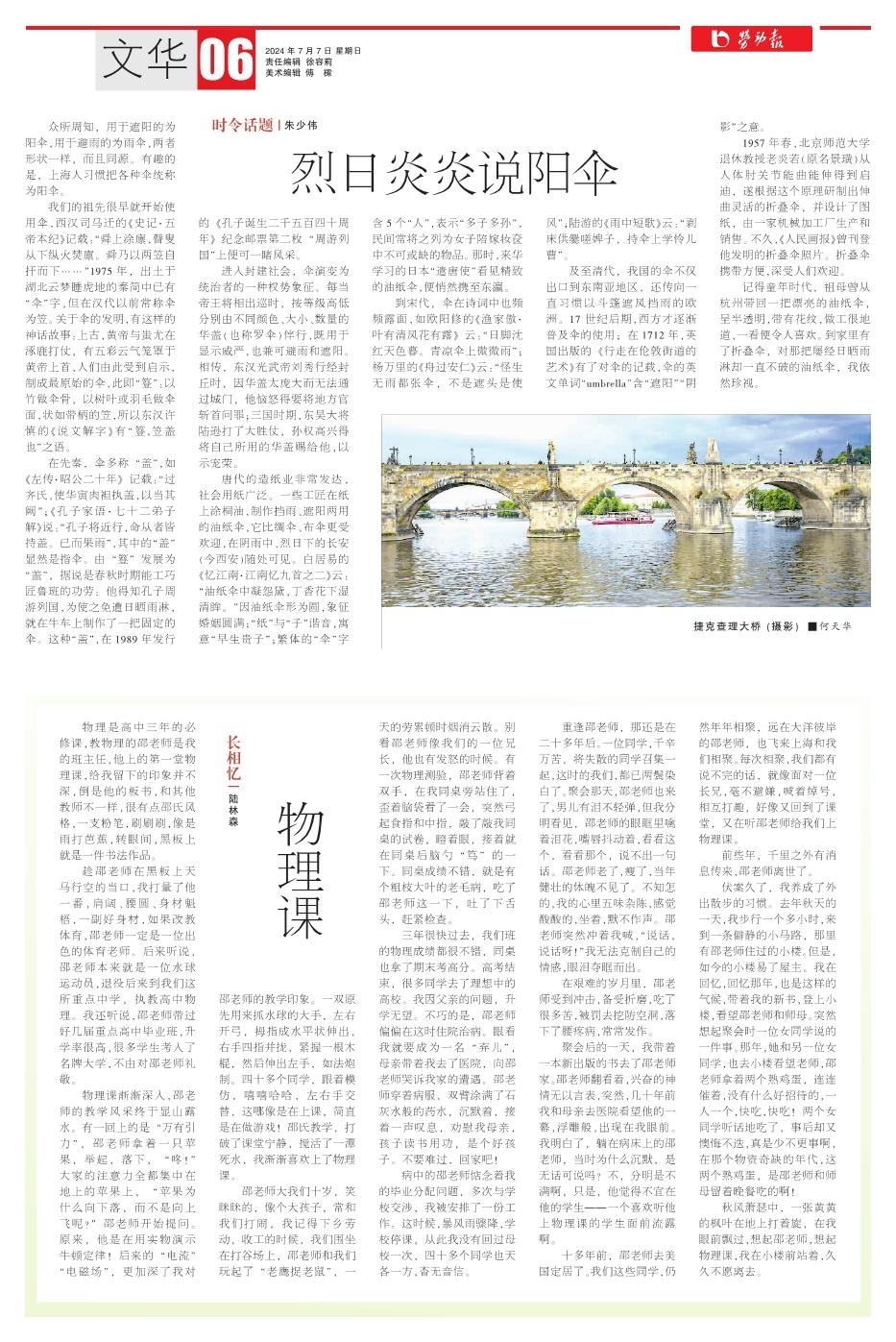图为《撑阳伞的女人》(局部) 莫奈
众所周知,用于遮阳的为阳伞,用于避雨的为雨伞,两者形状一样,而且同源。有趣的是,上海人习惯把各种伞统称为阳伞。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使用伞,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中已有“伞”字,但在汉代以前常称伞为笠。关于伞的发明,有这样的神话故事:上古,黄帝与蚩尤在涿鹿打仗,有五彩云气笼罩于黄帝上首,人们由此受到启示,制成最原始的伞,此即“簦”:以竹做伞骨,以树叶或羽毛做伞面,状如带柄的笠,所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有“簦,笠盖也”之语。
在先秦,伞多称“盖”,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过齐氏,使华寅肉袒执盖,以当其阙”;《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说:“孔子将近行,命从者皆持盖。已而果雨”,其中的“盖”显然是指伞。由“簦”发展为“盖”,据说是春秋时期能工巧匠鲁班的功劳:他得知孔子周游列国,为使之免遭日晒雨淋,就在牛车上制作了一把固定的伞。这种“盖”,在1989年发行的《孔子诞生二千五百四十周年》纪念邮票第二枚“周游列国”上便可一睹风采。
进入封建社会,伞演变为统治者的一种权势象征。每当帝王将相出巡时,按等级高低分别由不同颜色、大小、数量的华盖(也称罗伞)伴行,既用于显示威严,也兼可避雨和遮阳。相传,东汉光武帝刘秀行经封丘时,因华盖太庞大而无法通过城门,他恼怒得要将地方官斩首问罪;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陆逊打了大胜仗,孙权高兴得将自己所用的华盖赐给他,以示宠荣。
唐代的造纸业非常发达,社会用纸广泛。一些工匠在纸上涂桐油,制作挡雨、遮阳两用的油纸伞,它比绸伞、布伞更受欢迎,在阴雨中、烈日下的长安(今西安)随处可见。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忆九首之二》云:“油纸伞中凝怨黛,丁香花下湿清眸。”因油纸伞形为圆,象征婚姻圆满;“纸”与“子”谐音,寓意“早生贵子”;繁体的“伞”字含5个“人”,表示“多子多孙”,民间常将之列为女子陪嫁妆奁中不可或缺的物品。那时,来华学习的日本“遣唐使”看见精致的油纸伞,便悄然携至东瀛。
到宋代,伞在诗词中也频频露面,如欧阳修的《渔家傲·叶有清风花有露》云:“日脚沈红天色暮。青凉伞上微微雨”;杨万里的《舟过安仁》云:“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陆游的《雨中短歌》云:“剥床供爨嗟婢子,持伞上学怜儿曹”。
及至清代,我国的伞不仅出口到东南亚地区,还传向一直习惯以斗篷遮风挡雨的欧洲。17世纪后期,西方才逐渐普及伞的使用;在1712年,英国出版的《行走在伦敦街道的艺术》有了对伞的记载,伞的英文单词“umbrella”含“遮阳”“阴影”之意。
1957年春,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老炎若(原名景璜)从人体肘关节能曲能伸得到启迪,遂根据这个原理研制出伸曲灵活的折叠伞,并设计了图纸,由一家机械加工厂生产和销售。不久,《人民画报》曾刊登他发明的折叠伞照片。折叠伞携带方便,深受人们欢迎。
记得童年时代,祖母曾从杭州带回一把漂亮的油纸伞,呈半透明,带有花纹,做工很地道,一看便令人喜欢。到家里有了折叠伞,对那把屡经日晒雨淋却一直不破的油纸伞,我依然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