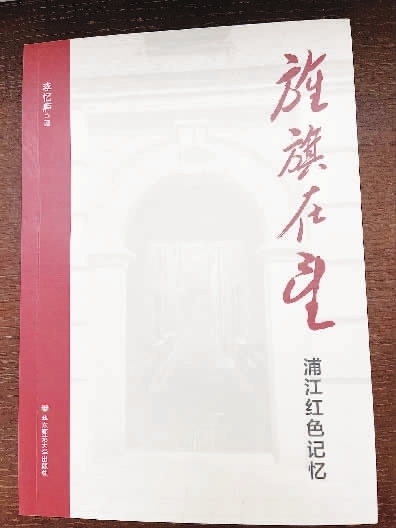
最近,我收到一本《旌旗在望》,取名于毛泽东的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里的句子:“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好大的气派啊!作者是李忆庐。
早几年在一些报刊杂志上看到一些文史方面的文章,与我研究的课题很接近,作者是李忆庐,后来我才知道,李忆庐就是我的好友李红。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笔名叫忆庐?”她回答:“因为我的家乡在安徽合肥,古时候称庐州。”这是表示怀念庐州。原来如此!
2009年李红从华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毕业,不久进入上海市档案馆工作,此后长期从事该馆的馆刊编辑工作。由于在档案馆里接触了丰富的文史资料,如鱼得水,给她写文章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是也有烦恼,资料多,必须去伪存真,必须研究分析,必须严密地考证……这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鉴别能力才行,她努力、努力、再努力,力求做到自己满意,也能让读者满意。
李红因要编杂志,不可能花大块时间写长文章,于是就采用“小而美”的方式。说实话,文章越小越难写,但她做到了。
在《为了忘却的记忆——左联五烈士书稿密存之谜》中,谈到白莽,即殷夫的诗稿《孩儿塔》,就处理得很好。
殷夫生前将1924年至1927年秋的诗作共65首,编成诗集《孩儿塔》,署名白莽,打算公开出版,托人送呈鲁迅先生审定,并请作序。可是我看到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孩儿塔》未完全发表诗稿。我在1983年4月12日《报刊文摘》发表的《殷夫的遗诗〈孩儿塔〉全部发表》。这是指1983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7辑上,第一次发表了《孩儿塔》65首诗中未刊的遗诗。我父亲丁景唐特地在这一辑中写了一篇《关于殷夫(白莽)遗诗〈孩儿塔〉的说明》。我在1984年为展望出版社写的《殷夫传》里也说到了《孩儿塔》,可是我一直不知道鲁迅是如何将这些珍贵的遗稿保存下来的。
感谢李红依据史料查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鲁迅先生逝世后,当时进步青年组成的列行社准备出版《孩儿塔》,许广平女士亲自从存放在英商麦加利银行保险库里的鲁迅遗稿中找出白莽的手稿,抄了一个副本交给列行社。然而,这个出版计划没有实现。
上世纪50年代这些左联五烈士的遗稿由许广平转交给鲁迅弟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再由冯雪峰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巧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父亲到北京开会,通过中央文化部的介绍,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孩儿塔》的全部手稿。
在《旌旗在望——新四军中的“上海兵”》一文里说到谭震林,这使我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那时正在与他的儿子谭大兵谈恋爱,时而会听到一些有关谭将军的事。听说谭的部队里有不少上海兵,具体情况不了解,看了李红的书后,才知道一些详细的事情。
为了壮大新四军的力量,1940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接到地下党的指示,把上海的有志青年学生和失业工人送到皖南和“江抗”(即新四军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参军,这是一支潜在的抗日有生力量,这引起了当时任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谭震林的注意。
1940年六七月间,谭震林决定不再由上海地下党成批向“江抗”输送新兵,改由“江抗”派人员打入上海去扩军。从东路到上海成为谭震林扩军的一个创举。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上海地下党的暴露,而且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大量输送兵员。怪不得谭震林部队里有那么多的上海兵。
思绪从书上收回来,眼光又落在了作者的名字上。忆庐这个名字固然有其寓意,但我更喜欢李红这个名字,红红的李子、红红的天、红红的地、红红的人、红红的书,愿作者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正能量的新书出版,我们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