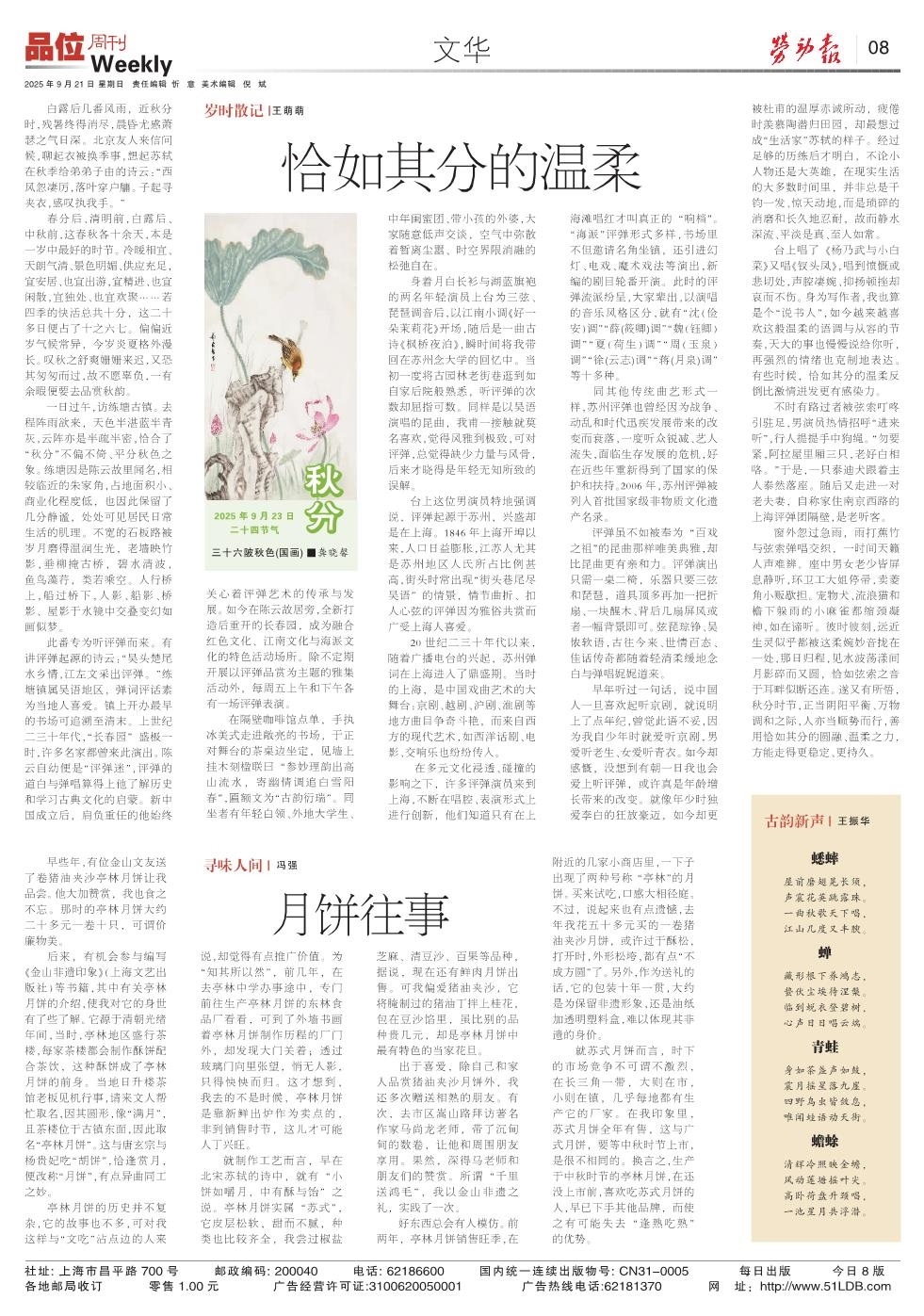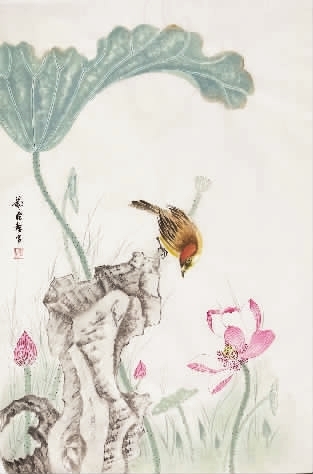
白露后几番风雨,近秋分时,残暑终得消尽,晨昏尤感萧瑟之气日深。北京友人来信问候,聊起衣被换季事,想起苏轼在秋季给弟弟子由的诗云:“西风忽凄厉,落叶穿户牗。子起寻夹衣,感叹执我手。”
春分后、清明前,白露后、中秋前,这春秋各十余天,本是一岁中最好的时节。冷暖相宜、天朗气清、景色明媚、供应充足,宜安居、也宜出游,宜精进、也宜闲散,宜独处、也宜欢聚……若四季的快活总共十分,这二十多日便占了十之六七。偏偏近岁气候常异,今岁炎夏格外漫长。叹秋之舒爽姗姗来迟,又恐其匆匆而过,故不愿辜负,一有余暇便要去品赏秋韵。
一日过午,访练塘古镇。去程阵雨欲来,天色半湛蓝半青灰,云阵亦是半疏半密,恰合了“秋分”不偏不倚、平分秋色之象。练塘因是陈云故里闻名,相较临近的朱家角,占地面积小、商业化程度低,也因此保留了几分静谧,处处可见居民日常生活的肌理。不宽的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生光,老墙映竹影,垂柳掩古桥,碧水清波,鱼鸟藻荇,类若乘空。人行桥上,船过桥下,人影、船影、桥影、屋影于水镜中交叠变幻如画似梦。
此番专为听评弹而来。有讲评弹起源的诗云:“吴头楚尾水乡情,江左文采出评弹。”练塘镇属吴语地区,弹词评话素为当地人喜爱。镇上开办最早的书场可追溯至清末。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春园”盛极一时,许多名家都曾来此演出。陈云自幼便是“评弹迷”,评弹的道白与弹唱算得上他了解历史和学习古典文化的启蒙。新中国成立后,肩负重任的他始终关心着评弹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如今在陈云故居旁,全新打造后重开的长春园,成为融合红色文化、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特色活动场所。除不定期开展以评弹品赏为主题的雅集活动外,每周五上午和下午各有一场评弹表演。
在隔壁咖啡馆点单,手执冰美式走进敞亮的书场,于正对舞台的茶桌边坐定,见墙上挂木刻楹联曰“参妙理韵出高山流水,寄幽情调追白雪阳春”,匾额文为“古韵衍瑞”。同坐者有年轻白领、外地大学生、中年闺蜜团、带小孩的外婆,大家随意低声交谈,空气中弥散着暂离尘嚣、时空界限消融的松弛自在。
身着月白长衫与湖蓝旗袍的两名年轻演员上台为三弦、琵琶调音后,以江南小调《好一朵茉莉花》开场,随后是一曲古诗《枫桥夜泊》,瞬时间将我带回在苏州念大学的回忆中。当初一度将古园林老街巷逛到如自家后院般熟悉,听评弹的次数却屈指可数。同样是以吴语演唱的昆曲,我甫一接触就莫名喜欢,觉得风雅到极致,可对评弹,总觉得缺少力量与风骨,后来才晓得是年轻无知所致的误解。
台上这位男演员特地强调说,评弹起源于苏州,兴盛却是在上海。1846年上海开埠以来,人口日益膨胀,江苏人尤其是苏州地区人氏所占比例甚高,街头时常出现“街头巷尾尽吴语”的情景,情节曲折、扣人心弦的评弹因为雅俗共赏而广受上海人喜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随着广播电台的兴起,苏州弹词在上海进入了鼎盛期。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大舞台:京剧、越剧、沪剧、淮剧等地方曲目争奇斗艳,而来自西方的现代艺术,如西洋话剧、电影、交响乐也纷纷传入。
在多元文化浸透、碰撞的影响之下,许多评弹演员来到上海,不断在唱腔、表演形式上进行创新,他们知道只有在上海滩唱红才叫真正的“响档”。“海派”评弹形式多样,书场里不但邀请名角坐镇,还引进幻灯、电戏、魔术戏法等演出,新编的剧目轮番开演。此时的评弹流派纷呈,大家辈出,以演唱的音乐风格区分,就有“沈(俭安)调”“薛(筱卿)调”“魏(钰卿)调”“夏(荷生)调”“周(玉泉)调”“徐(云志)调”“蒋(月泉)调”等十多种。
同其他传统曲艺形式一样,苏州评弹也曾经因为战争、动乱和时代迅疾发展带来的改变而衰落,一度听众锐减、艺人流失,面临生存发展的危机,好在近些年重新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和扶持。2006年,苏州评弹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评弹虽不如被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那样唯美典雅,却比昆曲更有亲和力。评弹演出只需一桌二椅,乐器只要三弦和琵琶,道具顶多再加一把折扇、一块醒木、背后几扇屏风或者一幅背景即可。弦琵琮铮、吴侬软语,古往今来、世情百态、佳话传奇都随着轻清柔缓地念白与弹唱娓娓道来。
早年听过一句话,说中国人一旦喜欢起听京剧,就说明上了点年纪,曾觉此语不妥,因为我自少年时就爱听京剧,男爱听老生、女爱听青衣。如今却感慨,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会爱上听评弹,或许真是年龄增长带来的改变。就像年少时独爱李白的狂放豪迈,如今却更被杜甫的温厚赤诚所动,疲倦时羡慕陶潜归田园,却最想过成“生活家”苏轼的样子。经过足够的历练后才明白,不论小人物还是大英雄,在现实生活的大多数时间里,并非总是千钧一发、惊天动地,而是琐碎的消磨和长久地忍耐,故而静水深流、平淡是真、至人如常。
台上唱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又唱《钗头凤》,唱到愤慨或悲切处,声腔凄婉、抑扬顿挫却哀而不伤。身为写作者,我也算是个“说书人”,如今越来越喜欢这般温柔的语调与从容的节奏,天大的事也慢慢说给你听,再强烈的情绪也克制地表达。有些时候,恰如其分的温柔反倒比激情迸发更有感染力。
不时有路过者被弦索叮咚引驻足,男演员热情招呼“进来听”,行人提提手中狗绳。“勿要紧,阿拉屋里厢三只,老好白相咯。”于是,一只泰迪犬跟着主人泰然落座。随后又走进一对老夫妻,自称家住南京西路的上海评弹团隔壁,是老听客。
窗外忽过急雨,雨打蕉竹与弦索弹唱交织,一时间天籁人声难辨。座中男女老少皆屏息静听,环卫工大姐停帚,卖菱角小贩歇担。宠物犬、流浪猫和檐下躲雨的小麻雀都缩颈凝神,如在谛听。彼时彼刻,远近生灵似乎都被这柔婉妙音拢在一处,那日归程,见水波荡漾间月影碎而又圆,恰如弦索之音于耳畔似断还连。遂又有所悟,秋分时节,正当阴阳平衡、万物调和之际,人亦当顺势而行,善用恰如其分的圆融、温柔之力,方能走得更稳定、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