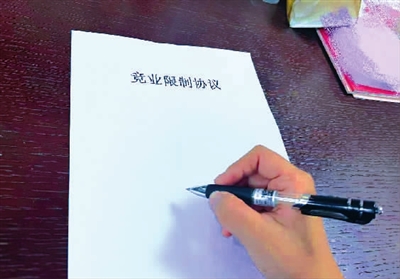
杨某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自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并由派遣公司派遣至A公司处工作,担任装运维工程师一职。同日,杨某与A公司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和保密协议,约定了竞业限制内容、期限及竞业限制补偿金等内容。2022年1月12日,杨某因个人原因向A公司提交离职申请,1月27日,A公司向杨某出具通知函,通知函中重申了竞业限制生效日期、期限、竞业限制区域、限制行业以及竞业限制补偿金,并要求杨某在竞业限制期内到任何新的用人单位任职,应向公司提交本人与新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杨某于1月28日办理了工作交接手续。2022年1月30日,A公司向杨某转账2590元,用途显示为“2月竞业限制补偿金”,后杨某将该笔费用退还。2022年2月8日,杨某入职B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担任装运维岗位工作。
2022年2月23日,A公司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杨某支付A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15万元,并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仲裁委裁决杨某向A公司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并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杨某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杨某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至A公司,A公司系用工单位,并非用人单位,将派遣员工作为竞业限制主体已超出了法律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工作岗位上实施的立法目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签订竞业限制主体的规定,A公司要求杨某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没有依据。
A公司不服,向中院提起上诉。
★争议焦点
A公司认为,只要劳务派遣员工的实际岗位掌握了用工单位的商业秘密,即可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杨某在职期间所从事的岗位需经过A公司委托合作公司的培训考核并颁发上岗证,装运维技术不为一般人所掌握,其知悉A公司的商业秘密,属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因此,杨某属于竞业限制义务适格主体。
杨某辩称,其系劳务派遣员工,A公司是用工单位,两者都不是竞业限制适格主体。他也只是一线操作工,所掌握的是最基础的知识,没有需要保密的内容。
本案争议焦点一是在于A公司是否属于竞业限制协议的适格主体,二是杨某是否需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法院判决:A公司未能举出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杨某属于竞业限制义务的适格主体,双方所签竞业限制协议无效,杨某自A公司离职后不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也无需支付A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
★点评
在劳务派遣这种雇佣与实际使用相分离的特殊用工情形下,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秘密的所有者和知悉者通常为实际用工单位和劳务派遣员工,虽然劳务派遣一般为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工作岗位,但这些岗位的员工并非完全接触不到商业秘密,用工单位与接触商业秘密的派遣员工之间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符合竞业限制制度的立法初衷。另外,劳动合同法虽然对劳务派遣作出了专门规定,但并未涉及派遣用工情形下的竞业限制问题,因此也不能得出禁止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的结论,用工单位也可以成为竞业限制协议的适格主体。就本案来看,关于杨某是否应当履行竞业限制义务,A公司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A公司具有特定的商业秘密以及杨某存在接触该些商业秘密的可能。最终,也正是因为A公司无法证明杨某属于竞业限制义务适格主体,故法院认定A公司与杨某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无效。
文何永强 摄朱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