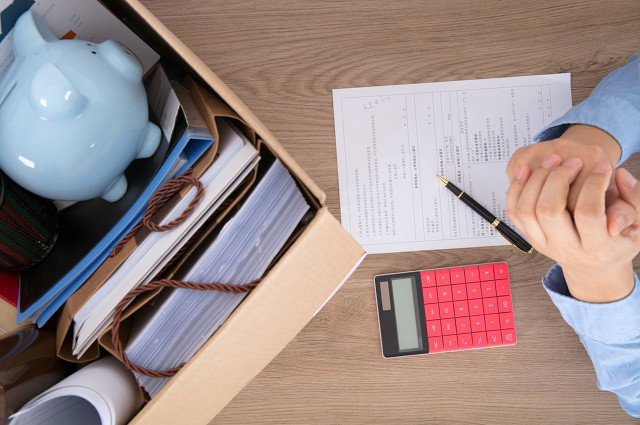
由于公司要求陶遵旨必须离职,他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因对裁决不满,他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时,陶遵旨提交的劳动合同显示,其合同期限为2018年4月24日至2021年4月23日,工作岗位系软件工程师。其提交的录音及文字记录还原了自己申请辞职时的情况。
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武某、行政经理张某在与陶遵旨对话时称:“其实,我们还是想要你好好地在这儿干,谁知道会这样?”“要不,你再让一步,一个月。”陶遵旨说:“那是10月份,你现在突然让我走,不是很搞笑吗?我那个时候有个项目总监职位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公司对该份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聊天者的身份信息无法确认,亦无法看出曾挽留过陶遵旨。
为证明自己一直在公司工作,陶遵旨还提交工作交接单予以证明。该交接单提交日期为2020年1月3日,证明其于2020年1月2日下午通过钉钉将工作文件发送给公司副总经理赖某,公司对该交接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称其是单方制作,不具可信性。
公司认可陶遵旨的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25000元/月+3000元绩效考核,但对其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员工每月应发工资数额承担举证责任,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采信陶遵旨的月平均工资28000元的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陶遵旨提出辞职申请后,公司应在30日内作出明确答复。因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已于2019年11月25日前答复陶遵旨准予离职,亦未明确通知陶遵旨离职的时间为2020年1月2日,在陶遵旨继续提供劳动、公司正常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其辞职申请作废,双方已就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协商一致。鉴于双方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公司于2020年1月2日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构成违法解除,应当支付陶遵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工资等。
根据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付陶遵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及2020年1月1日至2日的工资等121878.14元。
单位擅自附加条件,不能限制辞职权利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依据双方在一审期间的举证、质证及公司在上诉状中的陈述,认定以下事实:《辞职申请书》内容系公司人事部书写,但无证据证明已将相关内容通知陶遵旨。《员工手册》虽加盖有公司公章,但无证据证明已将相关内容通知陶遵旨或向其发放了该《员工手册》。另外,公司向陶遵旨支付了2019年11月、12月的工资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用。
二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法》第37条、《劳动法》第31条均规定,劳动者有职业选择的自由,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即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公司要求陶遵旨辞职需提前2个月书面提出,系对其行使法律规定的单方辞职权进行限制,该规定如果未与其协商一致,非其自愿接受,其内容没有约束力。
再者,公司没有证据证实陶遵旨接受了公司设定的附加条件。争议双方持有的劳动合同约定,陶遵旨若离职需提前1个月提出。而公司单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员工手册》与上述内容不同,规定部门管理人员辞职需提前2个月提出。即使该《员工手册》是真实的,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已向陶遵旨发放了该《员工手册》,或者至少已向其明示了上述要求。然而,公司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应认定双方并未就辞职需提前2个月申请的内容达成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事实,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1月2日解除的证据更具优势。陶遵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离职到期通知、工作交接单、谈话录音等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其申请离职未获批准,双方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直至2019年年末。而公司证明其主张的主要证据是陶遵旨的《辞职申请书》,且其自认离职日期栏目中“预计12月31日离职正常交接”内容系人事部填写。该申请书由公司保存,不能排除上述内容系事后变造,也没有证据证明公司确已通知陶遵旨同意其离职及办理离职手续的日期,该书证的证明力与对方提交的系列证据比较,显然处于劣势地位,不足以反驳对方的主张。另一方面,陶遵旨完成的2019年11月、12月份工作内容也证实其仍在正常工作,并没有办理离职交接手续。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判决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判。